美丽的邂逅(原创投稿: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)
美丽的邂逅
文:董玥/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
沐恩姐,江西南昌人,真名朱欢。第一次见沐恩姐,是在改稿会报到的那天,一个晴朗的午后。少年儿童出版社十楼,我们都在找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。她皮肤白皙,彼此问好时一低头露出一抹腼腆的浅笑。在等待前往湖州采风大巴的一段时间,我坐在楼前小院的座椅上,只顾和前来送行的朋友聊天,并未与她有任何交谈。只记得她将行李箱放于脚边,仰头看梧桐树叶间穿行的光束和澄澈的青空,很安静。
三个小时的车程,我们是邻座。各自拆开信封,浏览了行程安排表和大家的稿件(之前已看过电子版),她说她很喜欢我《记忆深处的那片星光》,具有八十年代学人生活的气息。这种情境正是我创作时精心构思并渴望向读者传达的,并不知成熟与否,她如此确切的表述让我颇感诧异。那时车已行出上海,天边集聚起浅红的云霞,聊天话题多了一些。我发现,她总在相视一笑的最后一秒蓦地屏声敛气,有如一段轻快乐曲猝不及防的收场。又交谈了几句,关于复旦的校园生活,关于中信出版集团的工作,清淡又客气。而后我插上耳机,点开网易云,进入另一维度的世界。
到达湖州芭提雅度假营地时,同拿到一张203房卡。如此短促的时间内,两个萍水相逢的个体可以接连产生交集,不得不说源自一种奇妙的缘分。到达当晚大家去娱乐室玩《孝衣新娘》剧本杀,她扮陈阿巧,我扮廖雲凌,都不是重要人物。开小差刷微信时,看见她刚发一条朋友圈,措辞简略严谨,喜悦中透漏着谨小慎微的心思。我更想结交爽脆豁达之人,因此不觉间与她的距离感似又加深了一分。
女生间的情谊总很微妙。或许是温热的空调松动了戒备,或许是山中明月夜拨动了沉寂良久的心弦,熄灯后浓郁的黑暗极容易过滤掉日光下秘而不宣的感知,保留一方安全且柔软的土壤。当一方尝试着敞开心扉,一句话,一个词,哪怕一点细微的停顿,彼此也是可以觉察得到的。我未曾料想到她率先迈开了第一步。是如何开始的呢?应是她娓娓向我诉说曾孤身在京漂泊的苦涩,创作梦想与世俗要求相碰撞的自我质疑,抑或如今平和如水深自缄默的心境。我倾听着,惊诧且惶恐,不知自己何处博得了对方的好感,竟可以受到如此诚挚的礼遇。窗外山峦连绵,不远处的亭台隐约传来古琴弹唱,风声穿过竹林映现出星火的美丽。
我想起陶诗“日入室中暗,荆薪代明烛”,真恍如置身世外桃源,心中无所羁绊,只需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。前一阵内底郁结的愁思似乎并不重要了,如同云母笺上晕染的墨迹,均化作山石嶙峋边沿上的点点青苔。原来我们是如此相像之人,她在回忆彼时彼刻的心境时,甚多波动且渺远的情绪竟会与我的此时此刻无缝对接。一个在二十岁的起点兀自茫然,一个正迎向三十岁的笃定与看淡。她说向往八十年代学人生活,我们对话的起始,还记得吗?突然就明白了为何她能够领会,因为这就是她的生活本身啊。工作之余,去北大听文史讲座、去故宫博物院、中国美术馆、先锋话剧院、老北京天桥艺术中心、798艺术区……一边是面包,一边是梦想,在两者间来回穿梭,疲惫且知足。
事实上,这段时间我掩下了太多纷乱思绪。寻觅不到倾诉的对象,除了远在故乡的妈妈,不想让她徒然牵挂。这种极私密的情绪宣泄,有如主动缴械褪下铠甲,一旦被回击便手无缚鸡之力。不,并非回击,不被理解就够了。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,理解谈何容易?在完全袒露的状态下孤注一掷,再次体验被侵蚀放大了数倍的痛苦,宁可没有开始。“当你专注于精神世界的构建,拼尽全力追寻心中的一些召唤时,孤独是必然的。”我不畏惧孤独,但不堪它所带来的自我质疑的焦灼。无人鼓掌,无人抚慰,无人知晓。
她转给我一个链接,“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,智慧而脆弱,一点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,一点点漠视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”,阿忆的《我的生死北大》。选择学人生活,就得承受起它的智慧而脆弱。“生活不必拘泥,踏实做事无愧于心就好,”她说:“你要知道,活着,就已经很勇敢了。”
晨光洒满房间时,我们前往十里银杏长廊漫步。秋日微凉但并不萧瑟,山水遥迢间自有一番清冽的诗意。大约十年前吧,她开始尝试创作,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北京南锣鼓巷一家民营出版公司:后浪。“在这里,我看见一种梦想,一种初心:那是出版业的一种坚守……在后浪,我看见许多优秀的人们,他们默默无闻、十分执着近乎倔强地坚守着一种东西。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它,那近两年的时光,带给我太多的感动与快乐。从他们身上,我学到了许多,就像史铁生的《务虚笔记》里的‘生日’,可能一种观念诞生的时刻,它也是一个盛大的生日。”
然而,男权社会并不会给予女性太多包容与善意,她终究选择了离开。入不敷出的薪水、辗转繁复的通勤、父母催促她回家成婚的压力……回到南昌,参观登记在她名下的三居室,与在京的蜗居两相对比,瞬间迸溅出剧烈的魅惑:古雅清静,坐北朝南,这未尝不是一个适合创作的好地方?
正如《半生缘》的结局,多年后再相逢,曼桢对世均说:“我们回不去了。”从大学离家读书到如今已近十年。她亦回不去了。收拾行装,去上海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,她最终回到北京。站在地铁口看列车来了又走,载离一波波涌动的人潮。四海茫茫,何处是吾乡?当得知“第二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”征文消息时,她几乎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:就这一次了,不能就彻底放弃吧。用家里的钱支持在北京的生活,这是一种毫无自尊的、追求梦想的姿态。
“十年,感谢给我机会上场。”她的《沐恩奇遇记》获奖,并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。那年年底,她以此为跳板成功入职中信出版集团,一跃实现经济独立,开启了事业新蓝图。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,娇小羸弱的女生,笑起来仿佛惊慌的小兔子,目光澄澈到令人怜爱。初遇时只隐约觉出她的敏感多思而有心疏离(近来的颓丧让我变得刻薄),未曾想过或许正因于此让其拥有了比旁人更丰厚的东西。比如坚韧,比如纯粹,比如信念。
山风拂过耳际,心中积聚的阴霾似乎消散了一些。行经花海,成片的鹅黄、柚红、樱桃粉、宝石蓝无惧严寒交相辉映,上演着独属于自己的骄傲与盛大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她们的内心该是强大的。很多问题只要你忽略,就不复存在了。“有没有掌声不重要。鼓掌的人不一定真心,甚而会出于一种恶意的引导。孤独,反而是最安全的。”她侧身握住我的手,轻软温热。时近正午,目光所及处几户农家已升起袅袅炊烟,两只小黄狗在不远处的藩篱下戏耍,一切恍然如梦中。
其实,任何相遇都有如一份奇异恩典,人生中遇见谁不是为了承前启后呢?上帝说,要有光,于是便有了光。在我最困囿的时刻,在这群山环绕的世外桃源,或许,沐恩姐就是那一束熙暖而有力量的光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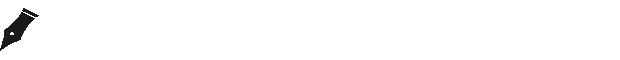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起.jpg)
